那玩意儿有抹勾魂摄魄的紫光。在昏暗的地穴深处幽幽发亮,躺在冰冷的石台上,像凝固的星辰碎片。多少双眼睛为了它熬得通红,在摇曳的火把光里死死盯着,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贴上去看个清楚。
总有些声音在角落飘着说这玩意儿有啥用。费那老鼻子劲钻古墓,熬得眼袋快耷拉到下巴颏,就为了块发光的石头。有这功夫,干点啥不好。这话听着耳熟吧,像老和尚念经,嗡嗡嗡的。
该钻的坑道还得钻,该趟的毒水还得趟。祭坛深处,法师袍子被魔法乱流撕开几道口子,汗珠子砸在滚烫的魔法阵上滋啦作响,眼睛还是死死粘在祭坛中心那一点紫光上。心跳得跟打鼓似的,就盼着那阵强光闪过,手里能多份沉甸甸的踏实。
有老哥揣着它蹲在安全区的墙角,一遍遍摩挲,指头肚儿感受着螺壳上每一道细微的凹痕。那紫光仿佛能吸走周遭所有的嘈杂,就剩下自个儿的心跳声。值不值。这念头也就一闪,指头早就不听使唤地把它又揣回最贴身的口袋里,捂得热乎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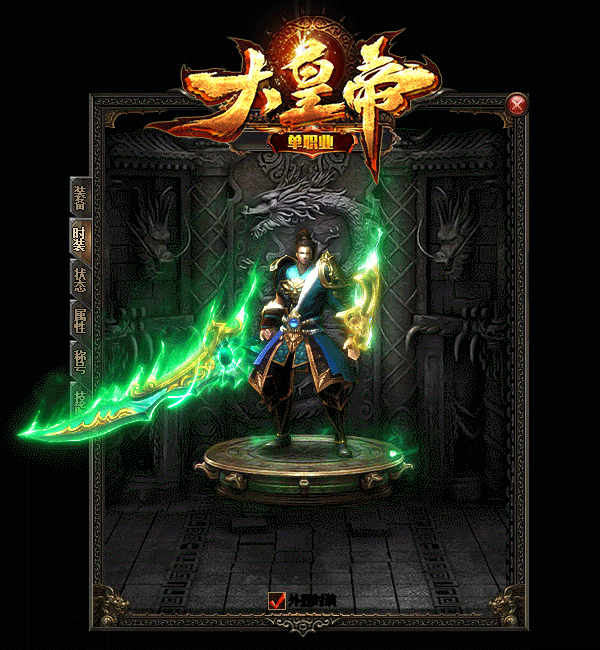
外头的人觉得咱们泡在里头是虚度光阴,是傻子。他们哪懂,当那紫光终于从祭坛喷涌,稳稳落在手心那一瞬。全身的骨头缝里都像灌了滚烫的岩浆,所有的疲惫都蒸发了,只剩下难以言说的冲顶快意。这感觉,外头那些指手画脚的人,一辈子也尝不到。
这紫色的小东西,从来就不是块简单的石头。它是无数个深夜的守候,是汗水浸透的衣襟,是心跳如鼓的狂喜。它静静地躺在掌心,紫光流转,映着主人疲惫却明亮的眼。那些说耽误工夫的声音,在它的光芒里,显得那么轻飘。它成了某种隐秘的刻度,标记着主人独自穿越的漫长黑暗。每道磨损的纹路里,都凝固着只有自己才懂的夜晚,那些与寂静为伴,只为等待一道紫光刺破虚无的执着时光。
